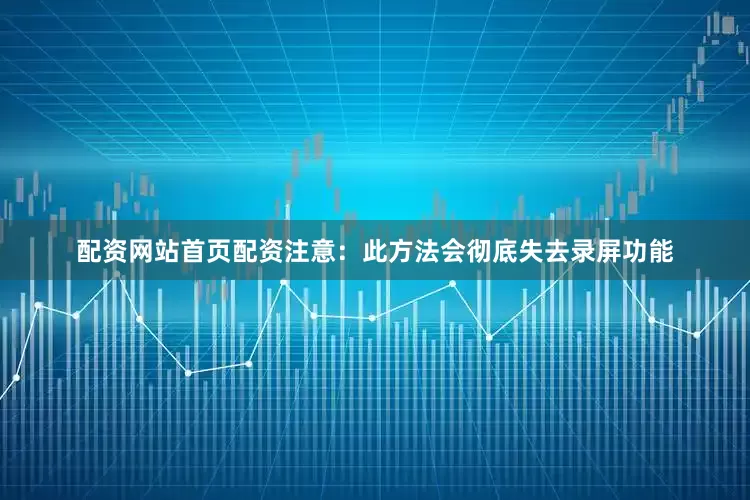日期:2025-10-16 09:19:19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写出了一个全书最重要的点,那就是“存在”和“获致优良生活”的条件分别是什么,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政治制度的“代名词”)应该是一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志同道合”的公民,为了达成“自足而至善的生活”,聚集起来形成的“公民集团”所维持的政制。这种“政制”的形式仍然是法治为主,人治为辅,而法治倚靠的仍然是“分权与制衡”。
这一部分我在上一篇《亚里士多德的“好公民”“正常政体”与“法治”,无论外部解释力如何,内部确实是自洽的》已经写过了,其实“臭皮匠集团军”的设置,也是一种权力的制衡关系,只不过,这种“萌芽”很小,不容易让人看到,所以也没人总结出来。
权力分置与制衡的原则,对于英美都是很重要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述中也很多,“集体异人”与“少数贤良”之间的“对峙”就是一个例子。而对他来说,如果不把集体异人们放进去,就会造成树敌众多的恶果,因此,与其建立正式的敌人,不如创造融入建制的“反对派”,反对派与执政派之间,又是一种制衡,只是它并非制度性的,而是动态的一种现象,但也无法否认其中存在分权与制衡的作用。
总结起来,就可以说“集体异人”与“少数贤良”形成了制度性的相互约束,而朝野两派则具有不稳定、非制度性约束的功能,所以,开个玩笑,按照西方人喜欢到处“认祖归宗”的习惯,分权与制衡其实不应该从英国中世纪的《大宪章》里去寻章摘句,而是多拜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好。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边走边说言归正传,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亚里士多德对政治两大元素——“存在”(即自足)和“优良生活”(至善)的构成物的论断。他认为自足需要财富和自由,这与之前亚里士多德所写的“素朴”且“丰裕”的生活等于“自足”的判断是一致的。这里的自由,当然不是纵欲,胡吃海塞,吃喝嫖赌,而是合乎自然伦理,也就是自然法的精神——量入为出,满足基本需求即可,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呢,他又不赞同节衣缩食到寒酸的地步,所以,相对富裕的资财,对于维持一个家庭、一个城邦的运转,无论是从冗余准备看,还是非持续性的改善伙食、衣用,都是有很重要的价值的。
中世纪欧洲书籍中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插画

更关键的是“至善”的部分,这里讲究的是“优良的生活”。至善在政治学里,仅就亚里士多德而言,就是追求某种程度的正义,这种正义更具体的说,就是在某种情境下对于某种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和平等性。结合我们之前看到的共和、贵族与君主诸政体,这种至善,其实就是统治者在理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心性,掌握两种政治品德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平衡各方的利益,用一个时髦点的词来说,就是尽量达成帕累托最优。
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乃至连被统治者的地位都没有资格获取的群体,例如外邦人和奴隶,是有等次之别的,这种差别使得他们的利益、义务与道德都是不同的,只要满足了这个“梯田格局”的政治需求,那么这个统治者就可以被这个斯塔基拉人所称赞为正宗政体的执行者了——践行了政治的善。除了君主制外,贵族和共和,都要求存在“轮番而治”可能性的阶层内部要履行一种“妥协的道德”,即便君主制,其实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也是包含这层意思在的。
下图展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学院吕刻昂(Lyceum),吕刻昂学园与柏拉图的学院不同,提供了许多向公众开放的讲座,并且是免费的。

唯此,君主也肯定需要代表一定阶层的利益,虽然决策权等权利不对他们开放,但君主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上存在的议会或会议,否则他就无法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哪怕它是一种橡皮图章。亚里士多德的差序等级结构,或者说用我创造的新词“梯田格局”,其实暗含了一点,那就是在君主制里,最为优种的阶层,其实是君主应当代表利益的最主要选项。

亚里士多德也被认为是伊斯兰哲学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而且,为了体现一定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翻转结构”,一种非正式的“轮番而治”也必须存在于君主决策的过程中,按照这个逻辑,其实宋朝的模式是最相宜的,因为弟煮階/级的精英被选拔上来,而且可以坐在椅子上和皇帝论道,并且他们的意见成为皇帝治国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几乎不可能被剔除的。而乡绅控制的“皇权不下县”的基层社会,则更成为这些精英的一言堂,无论是唐宋之前的门阀士族,还是之后依靠资财和科举名望而作威作福的乡绅,都是符合亚里士多德的理想的。
内藤湖南,最早提出“唐宋变革论”的学人

广瑞网-股票配资网站导航-专业炒股配资网-股票小账户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炒股炒股配资网在提及iOS26.1版本新增功能的章节中
- 下一篇:没有了